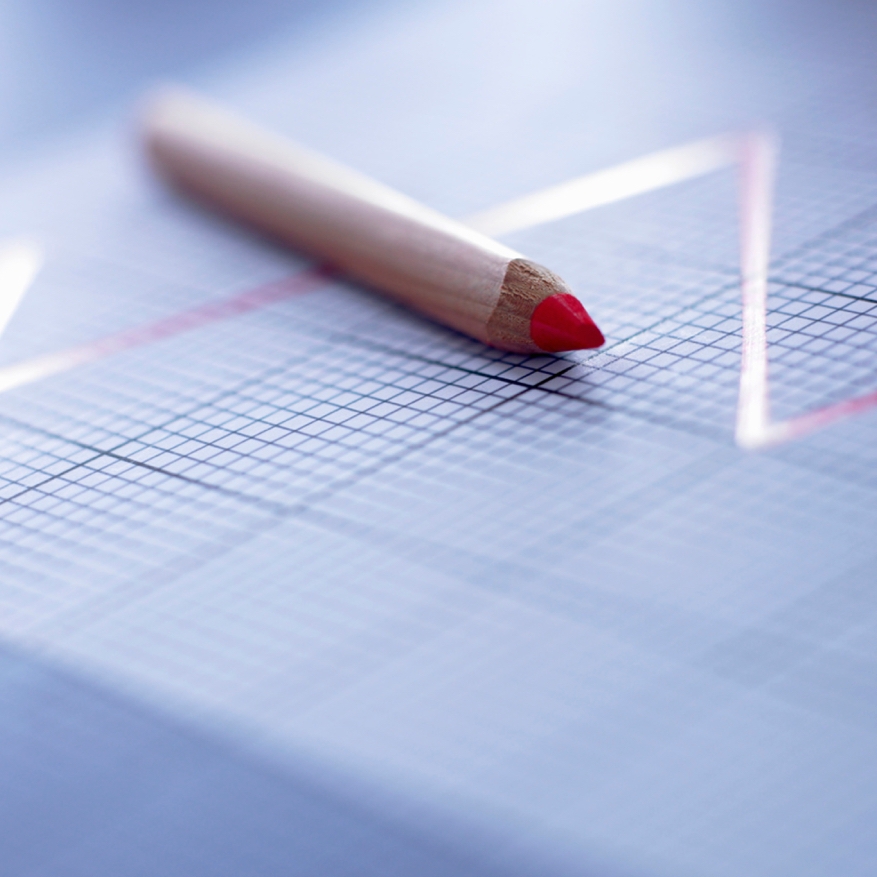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2.0的红利仍待释放。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以及更深层次的城市化,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过去半年,市场观察者对中国的信心以及经济判断的变化幅度非常戏剧性。
笔者在去年底提出,中国经济将在2019年上半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主要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中国逆周期政策发力,经济的相对走势“西方不亮东方亮”;第二,风险溢价,会出现柳暗花明,去年外部摩擦造成的信心冲击,伴随贸易协议的逐步明朗,会在今年峰回路转;第三,从国际资本流动看,会出现“一江春水向东流”,主要是源于美国经济寅吃卯粮结束后进入下行期,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转鸽,对新兴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产生利好。
目前来讲这三块均符合预期,部分印证了这一周期性拐点到来。
第一,经济相对走势。从去年11月、12月决策层加强逆周期调节以来,中国经济曙光初现。比如3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全球的指数普遍下滑,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指数跌到七年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反而复苏了。这反映了去年11月底以来与过往刺激道路不一样的逆周期政策慢慢取得效果,稳定信心。这个新式逆周期政策,采取比较公开透明的融资方式如地方债券,而非通过影子银行去增强稳基建调节力度,同时更多地采取了减税、减企业社保成本等来提振企业信心,并非仅限于传统的基建。
第二,风险溢价。去年风险溢价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外部贸易摩擦的上升。尤其到了下半年,市场对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极度悲观。然而,分析贸易政策,不能脱离全球政策决策者面临的短期约束,西方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务实、有短期诉求的。如果处于十年复苏晚周期的美国经济在2018年“寅吃卯粮”的财政刺激强心针之后进入显著下行期,那么其政界对于外部摩擦的应对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摩擦降级、达成一个双方共同能接受的贸易协议,符合共同利益,这带来了风险溢价好转、企业信心恢复。
第三,全球资金流动。去年下半年很多研究人士对于人民币贬值、资本流出颇为担忧,但是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一是外部的环境改善。全球央行转鸽,特别是美联储,不仅不加息,还会停止缩表,以至于市场甚至开始讨论降息的可能性。这从侧面支撑人民币汇率。第二个重要变量是中国呼之欲出的结构性新趋势,即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可能正式走上了快车道。
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大势所趋
笔者认为,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实体经济对外开放、深度城市化,是供给侧改革2.0阶段的三支柱。
随着储蓄率从2008年52%的高点下降到今天的45%,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由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向由消费拉动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经常账户从过去巨额的顺差慢慢回落,并可能在未来出现逆差。其他经历过人口老龄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经验。一方面,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逐步下滑。更重要的另一个层面,则是国际收支压力加大。顺势而行,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成为当务之急,且有望走上快车道。另一方面,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全球投资者需要到中国来。
从我国自身需求来看,2019年非常有可能是经常账户逆差元年,规模约占GDP的0.5%。但随着未来储蓄率的进一步下降,逆差的规模将逐渐扩大。如果资本账户也是逆差,那么双逆差可能会对外汇储备带来较大压力。据笔者估算,从2020年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逆差规模在2000亿美元左右,占GDP 1%。当然,笔者预判的经常账户逆差幅度相对有限——曾经出现过国际收支危机的新兴市场常有高达3%-5%的逆差。
另外,中国的对外净资产约为1.3万亿-1.4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可以充当缓冲国际资本流动的护城河。尽管如此,持续双逆差将导致外汇储备不断下降,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对中国国际收支稳定的判断也可能越来越接近其他新兴市场,这是关心中国的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的优势,在于过去40年的高增长积累了大量的资产,在岸债券和权益市场也已经相对深化。这些市场过去对外开放程度有限,但近来逐渐涌现诸多里程碑式事件。例如国内金融市场不断被纳入国际基准指数。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决策层在过去三年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市场改革,包括提升金融监管水平、清理影子银行、防范金融风险,更重要的就是对外开放。
笔者编制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路线图,发现过去三年之中,股市、债市、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方面的对外开放,每年都有新的进展。往前看,新的看点包括进一步增加便利的投资渠道(比如债市通、股市通),进一步增加风险管理对冲工具,以及在会计和税收等政策上与国际监管水平接轨。
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国际基准指数纳入中国债券和股市、或者进一步提高纳入因子。此外,随着《外商投资法》的通过以及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望保持现有的竞争力。
从全球投资者的角度,他们是否有兴趣呢?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人民币资产的收益从投资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极具吸引力。中国国债与美国国债之间的关联程度远低于日本、欧洲等,再加上中国国债收益率更高,这就为全球资产管理者提供了优质的分散风险的资产。
从过去两三年来讲,这种趋势已经逐步显现。当然目前主要是一些中央银行在买中国的国债,接下来主要新加入的投资者,就是国外的长线资金,特别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大学基金等。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外资持有比例不外乎2%,但是笔者预估未来5年-10年,随着中国在各种国际基准指数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全球投资者会逐渐加大对中国债市的投入,年流入量大概接近1000亿美元,其中一半是指数型基金,另一半是主动管理型投资者。此外还有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根据大摩全球股市策略团队的分析,大概带来的年新增规模也是在750亿到1250亿美元之间。债股叠加,至2030年证券投资的年均流入量在2000亿美元以上,足以覆盖经常账户的结构性变迁。
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才算真正启动。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占比将不断提升,从现在的2%上升到5%,超过日元和英镑,在储备货币地位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事实上这个估计仍属保守,因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包括中国经济体量占全球的比例均超过10%;债市、股市的规模都在世界前三。笔者认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拥有一席之地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局面:美元一家独大并非历史常态,从19世纪下半段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全球储备货币一直较为平均地分布在诸强之中。
供给侧改革2.0
过去三年的供给侧改革1.0阶段,决策层主要关注“三去一降一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控制了杠杆率,提升了产能利用率,全要素生产率也从低位回升。2.0阶段,还需回归本源和初心,持续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挑战。
除了上文提到的用好国际资本,还有两个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的手段。第一,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的对外开放。过去40年,中国每一次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周期,都与前期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力有关。
当前,中国吸引全球产业链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创新实力渐强,国际专利申请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供应链的复杂和分工程度领先全球;基础建设跟东南亚竞争对手相比优势明显;还有工程师红利,过去五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几乎相当于东南亚主要国家受到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总和。
摩根士丹利对33个行业和75家跨国公司进行的调研显示,尽管面临各种各样的成本上升、外部摩擦等原因,全球的产业链还是不想搬,也搬不走。即便在低附加值行业,譬如服装产业,过去十年搬走的也不多,且只有越南一个国家明显受益。
第二,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2.0理应包含深度城市化。很多人认为中国现阶段缺城市化后劲,实则不然。我国城市化的战略正在经历由依靠个别大城市,向依靠城市群转变,同时依赖更环保、更有效率的方式来促进城市化,包括更经济高效的高铁和城际铁路的互联互通。
事实上,中国人出行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靠城际铁路和高铁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2010年高铁网络大范围铺开之后。互联互通的好处之一,是城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譬如从摩根士丹利的香港办公室到深圳福田CBD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作为对比,同样的距离,从旧金山市中心的摩根士丹利办公室到硅谷,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互联互通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则更加深远。
笔者的研究表明,城际铁路大范围铺开后,长三角城市群内三四线卫星城的生产率改善幅度超过了核心的上海和杭州,知识的外溢和产业链的集群效应在城市群时代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2.0的红利仍待释放。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以及更深层次的城市化,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中间需要把国际资本用到位、用活,支持上述高质量的投资,即便人口老龄化,中国仍有望在未来五年保持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人均GDP将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二战以后,只有波兰和韩国两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以此为背景,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力仍值得期待。
*本文首刊于2019年4月1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